 创建时间:2023-07-12 23:20:42
创建时间:2023-07-12 23:20:42
 视频提供 :河北文艺网
视频提供 :河北文艺网

旭宇
旭宇是书家,也是诗人,此前我们是知道的。我们甚至知道作家管桦笔下那条还乡河,流经丰润,流经玉田,过净觉寺后,再向前不太远,傍河就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。我们甚至还知道他原来叫许玉堂。甚至由他这个名字我们想到了元人王恽《玉堂嘉话》和明人焦竑《玉堂丛语》中的故实。然而,无论如何,彼此相见,对话之余,看到具有视觉和心灵双重冲击力的“何黄会”,一场“三人行”般的粉丝聚会,我们是未曾想到的。

旭宇先生接受采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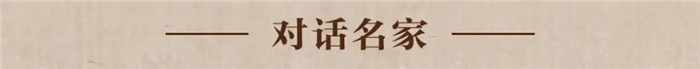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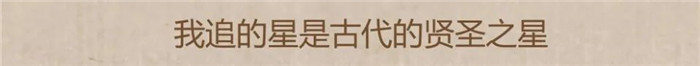
记者:您有很多著作。有一部与众不同,就是《寄给历史之书札》。
旭宇:2016年,《书法报》的主编在上海出的书法杂志上,看了我写给王羲之的一封信,感到很新鲜,说我们今天的人给1600年前的王羲之写信,信写得很短,但是很有内涵,他们很感兴趣。他们说,旭宇老师你在历史上的研究不光是书法,在其他领域也读了很多书,你能不能就以信的这种形式,多发表点看法?我说可以吧。因此,我思考我读过的书,在读书过程中,我对哪些人印象比较深刻,或是有所感悟,然后提出我的个人看法,用短短40个字、70个字,但不超过100字,来表述我对这个人的评价。出发点就是把我的所学,通过我写给古人的信表达出来。
记者: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老子的……
旭宇:老子的思想,我是在有意无意当中接触的。1967年,我上大学的时候,就读老子《道德经》。那时候是朦朦胧胧的,感觉很奇特。后来我当了兵,把《道德经》还带在身边,1976年到了文联工作,也一直在读老子。读到现在读了五十几年,一直没有放弃。
我读老子,首先是修身。《道德经》中有这么一句话,“修之于身,其德乃真”。我读老子,想既修其心,也修其志。我把自己的所学所得,所理解的东西,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要体现出来。在书法上、诗歌创作上、文学的评论上,甚至在我最近的绘画上,都体现了老子思想给予我的智慧。我感觉读老子晚年非常受益,就是把自己变成老子的粉丝。
记者:您也追星。
旭宇:追星很正常,我也追星。我是“两族”出身,其中就有一个“追星族”,我追的星是古代的贤圣之星,老子、孔子、屈原、司马迁、王羲之、颜真卿……这些人是我心中的明星,他们照亮着我。我可以做他们的粉丝。

2008年秋,旭宇先生在北苑书斋修改诗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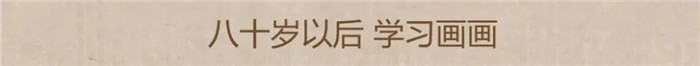
记者:80岁之后,您开始画画儿。
旭宇: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喜欢绘画。上中学的时候,老师就想把我培养成画家,但是因为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,就把这个爱好给“枪毙”了。后来,上了大学,我几乎把河北大学图书馆所有的画册、所有的书法集都翻阅了一遍。从那时起,我就对绘画有一种独特的想法。绘画和书法一样都是艺术,艺术应该传道。真正的艺术家得有责任心,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。
疫情期间,在家读书,有所感悟,我就用绘画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,因为绘画比较具象。
记者:在画儿上您还题了诗。
旭宇:如果说没有诗,没有情感,没有温度,那么这幅画就是没有生命的。我的绘画,我自己叫它文人画。因为我是个学生,是个文人,我追求的绘画和那些专业画家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是为了绘画而绘画,是为了载道而绘画,是追求一种思想,追求一种道德。所以我的每一幅画都有一个题目,都有一首诗,甚至是四首诗。诗和题目就传达了我为什么要画这幅画。
我没有想当个画家,现在也不是个画家。80岁以后学习画画,画得不好,但是表现了我的一种追求。

旭宇先生近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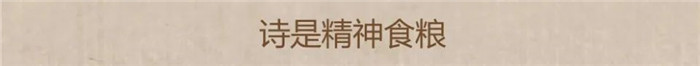
记者:最初,您被人认识,还是因为诗。
旭宇:我从中学时代就写诗。第一次发表诗是在1959年的《唐山劳动日报》。那时候能够在报纸上发表一首诗,是多么受鼓舞。学校同学们还朗诵过,在墙上贴过壁报。那时候的梦想是当诗人。我好多同学给我泼冷水,但是,我还是有这个梦。我要追梦啊。最后,还真成了诗人。
有的朋友说这诗人呢还不如卖油条、豆浆的,卖油条、豆浆还能够解决吃的问题,诗能解决什么呀。但诗是精神食粮,我们中国是诗的国度,不能离开诗。我新诗写得最多,从1958年开始写,一直写到现在。在写新诗之余,我更喜欢古典文学,喜欢唐诗、宋词、元曲,但是更多地喜欢古风。古风相对来讲比较自由,讲究文辞,基本上不讲究平仄。我写古诗词,大概算起来有三百首了。我偶尔写律诗,但是不主张写律诗。
诗言志。志应该有一个规范,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?这有个道的问题。艺术应该载道。
记者:《长城》杂志创办的时候,您担任了诗歌散文组组长。
旭宇:我转业的时候是1976年。我们河北省文艺组组长是大诗人田间,我愿意到这个单位来,他很欢迎。搞了几年行政工作后,就把我安排在新创刊的《长城》,任诗歌散文组的组长。
任这个组长,我想为河北乃至全国的中青年作家服务。不发自己的作品,要发就发青年朋友的作品,发全国有名的诗人的作品。我推出了“河北青年诗人十一家”,这“十一家”现在都活跃在河北的诗坛上,成为河北诗坛的骨干,乃至成为一代有名的老诗人了。
记者:后来您又当过《诗神》的主编。
旭宇:当时我在办《民间故事选刊》,很盈利,领导让去当《诗神》主编,把这个赚钱的刊物交给文联,我也没有怨言,欣然同意。既然我是个写诗的人,我去办这个诗刊也是一种归位。
记者:《诗神》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,你又交给了年轻人来接手。
旭宇:因为我相信青年朋友。你办得再好,也不能终生在这个岗位上。要知止。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应该有一种让贤的精神,文艺事业甚至所有的事业,都是日新月异,后浪推前浪。什么事都要落幕。尽管是落幕,我们还要有追求,还要精进,晚年不要松懈。

旭宇先生近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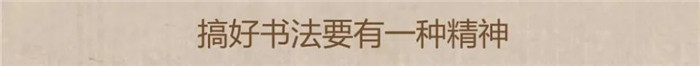
记者:说到诗,不能不说书法。您曾担任河北书协主席,您倡导“兰亭精神”,在业内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。
旭宇:这一晃二十几年了,河北那时处于书法事业低谷状态,书家们都很想改变现状。如何走出低谷?我就想办法,走群众路线。众人拾柴火焰高,我们在三年之内搞了三件大事。第一件是第四届全国新人展,这是国家级的展览;第二件是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;然后,又搞了中国书协首届学术研讨会。在这三大活动当中,河北的书法队伍形成了,群众力量形成了。这种情形之下,要搞好书法,把这些人培养成才,我觉得要有一种精神来指导。我提出了“兰亭精神”。
记者:其具体内涵是……
旭宇:第一是团结协作的精神。第二就是学术研讨的精神,切磋砥砺。第三点,就是治学,敬业,一起研究如何把艺术搞上去。兰亭精神是在河北需要的基础上,总结了当代书法的现状之后提出的。
记者:您还提出了“今楷”理论。
旭宇:这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我当中国书协副主席,兼楷书委员会主任。当时也做了调查研究的,因为参加全国的展览,看了好多的书体,感觉楷书被冷落了。人们都写行书,写草书,尤其是行草盛行,楷书入选率最低。人们都感觉楷书比较死板,一到国展的时候,评委们看这楷书都一个面貌,像印刷出来一样,没有神气。楷书要想振兴,要想符合时代精神,要想让这些书家和我们的时代能够契合起来,需要有一种新的动力和精神。
时代变了,要求楷书要艺术化,要有美感,要有个性,要能适合时代精神。我就在楷书委员会提出这个理念。唐朝人可以写出唐楷,北魏时写出了魏碑魏楷,我们能不能够写出今天人的审美追求,我们今天的楷书。我说我起个名字,叫“今楷”。

旭宇先生近照
记者:听说您编过一本《今楷论丛》。
旭宇:二十几个委员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观点,但是也有些委员有不同的意见。后来我说各位朋友辛苦一下,把你们的不同意见都写成文章,反对也好支持也好,咱们在报纸上进行讨论。在河南的全国性报纸《书法导报》上开了一个专栏。关于今楷的讨论非常热烈,公开讨论一年时间,最后支持的人还是绝大部分。我把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批评编了一本书叫《今楷论丛》,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公开发行。我从来不搞什么垄断,也不搞一家之言,我们这个讨论也是百花齐放。
今楷应该怎么写?我总结了几点。比如说楷书好比是站着的,行书是走着的,草书是跑着的,这个人站着立正是一个姿势,稍息也是个姿势,站着像模特一样摆个姿态也是站着,为什么不可以像模特一样摆个姿态让人很欣赏呢。这个楷书就是说在那不动,但是他可以做个姿态。今楷就要把楷书写得千姿百态,只要是楷书都行,你觉得怎么好看怎么写。

2006年3月,旭宇先生受西泠印社之邀题墨于孤山之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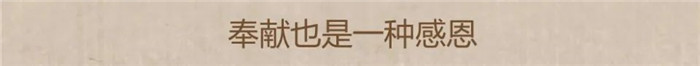
记者:您给自己定义为“两子”“两族”。
旭宇:其实人生啊,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目标。在这世上我走过了八十几年的时间,回顾过去,展望未来,我觉得我自己就是“两族”“两子”。两族第一族我是草根族。我特别欣赏一部书叫《菜根谭》,里边有深奥的哲学思想的表述,说要是自己能够理解自己是个草根子出身,那就不怕风不怕雨,坚持认清一种道路,继续前进。那么还有一“族”就是“追星族”。
“两族”与“两子”是密切相连的。好多人认为我是书香门第,我说非常不对,我就是农民家庭出身,我是农民的儿子。我今天能够取得一点成绩,感恩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培养了我。第二,我作为另一个“子”,就是“学子”,做一个终身的学生,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提高自己。在我个人看来,人品里最高的追求和修养是读书,读好书,读经典之书。人生能够读书才是最幸福的。一生能够与古人相伴,与经典相伴,与古人那种高境界的追求相伴,得到他们的启发,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。
我之所以80岁以后还继续画画儿,继续写诗,继续写书法,都源于读书。我现在最主要的修身就是读书。只有读书,你才能理解古人圣贤是怎么做的,我们应该怎么做。
记者:2004年以后,您向家乡玉田县以及博物馆、河北大学都捐赠过书法作品,还有珍贵的藏品。
旭宇:我好比是一个冰糕,冰糕上面有牛奶,有彩色的东西,有巧克力,中间就是一个木棍,我就是中间那个木棍。外边的牛奶呀,巧克力呀等等,这就是你所有的名声。教授啊,学者呀,书法家,诗人,这些外在的都是外加的东西。你的本体,你的本真,就是那个木棍。我总结了三句话:对上苍,对自然法则,要有敬畏之心;对于我们的社会,我们的历史,我们的文化,我们的祖国,我们的人民,我们的老师,要有感恩之心;对我个人而言,要有知足之心。
知足,又要知不足。对自己所取得的所谓的荣誉、地位,就要知足;知不足呢,要当一个学生,继续地学习下去。学习也包括奉献,这也是一种感恩吧。
(根据录音整理,有删节。)
(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 康瑞珍 李为华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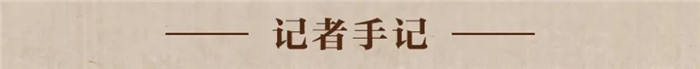
一场“三人行”般的粉丝聚会
杜甫说,“庾信平生最萧瑟,暮年诗赋动江关”。入过诗圣法眼的南北朝诗人庾信,宋人黄庭坚也青睐有加。黄庭坚是吟出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诗人,也是臻“凌云健笔意纵横”之境的书家,感铭于心,他曾手书庾信诗册。此书册传至清代,到了何绍基手上。“便拟荒鞋向山院,寻碑去扫荒莓苔”,何绍基是诗人,也是引领风尚的书家,黄庭坚此作,让他不仅见识了书家黄鲁直“笔情闲逸,不为过于遒肆,殆与诗同意”,神驰诗人黄山谷“作诗锤炼密栗,亦于开府有微尚焉”。打动他的还有更多,书法固然妙,但“观此册者,又岂徒重其笔迹之妙也哉”。
关公战秦琼,成为笑话,皆因为虚妄,现实中办不到。不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两个人打不起来,却有可能穿越,进行灵魂对话。倘若同道知音,便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。通过书写,黄庭坚与庾信进行了一场灵魂对话,同样通过书写,何绍基也与黄庭坚进行了一场灵魂对话。
黄庭坚的书册何绍基看到了,我们没看到。它是否尚存人世我们不得而知。欣赏何绍基与黄庭坚的灵魂对话,我们是通过另一件作品。
它是旭宇的珍藏。
士人的古雅最直观表现于其文其字。更有一种无形的古雅,漫溢于言谈举止之外,是通过与其相关的事或物展示出来。紫红色木制书案和书桌,茶几,相配套的太师椅和藤椅,博古架与木柜上的梅瓶和春瓶,青花瓷葫芦,一尊沁了光阴之色的白石佛首……旭宇家宽敞的客厅,最醒眼目的还是它——何绍基一件行书作品,内容乃黄庭坚一段颇具意味的书论节录:
……夫作字惟尚华藻,落笔不实,以风樯阵马为痛快,以插花舞女为姿媚,殊不解古人用意处……
与今天流传的本子比,何绍基所书,字句稍不同。主人说,原为四幅,首尾缺,存中间二幅,得之保定,原藏袁项城后人手。虽非完璧,然一眼望去,注意力便被甚深吸引。喜出望外,譬如追星,追到了何绍基,同时跟黄庭坚不期而遇。
旭宇是书家,也是诗人,此前我们是知道的。我们甚至知道作家管桦笔下那条还乡河,流经丰润,流经玉田,过净觉寺后,再向前不太远,傍河就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。我们甚至还知道他原来叫许玉堂。甚至由他这个名字我们想到了元人王恽《玉堂嘉话》和明人焦竑《玉堂丛语》中的故实。然而,无论如何,彼此相见,对话之余,看到具有视觉和心灵双重冲击力的“何黄会”,一场“三人行”般的粉丝聚会,我们是未曾想到的。
同为诗人书家,黄庭坚实践和理论并重,其启迪后生的心得,何绍基深契于怀,故下笔痛快沉着摇曳生姿神采飞扬,而这种契合,年逾八旬自称一介书生的旭宇先生当有戚戚焉。(刘学斤)